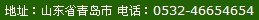|
虽然不容易,但大家又走过来一年了(三) 杨绛先生在百岁之年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认可,到 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样的格言需要通过生命践行的,岂是挂在墙上,贴在书桌角上就可以的。 不久前,和那位持续了八年的男士,完成了 一次会谈,给长长的咨询关系在年的年末岁尾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还剩几分钟时,我问他:“还记得吗?你 次来见我的时候,提出的咨询目标非常坚定,就是想消除‘抑郁症’。没想到,这么多年走下来,抑郁症并没有被我们消除,反倒是你完全能够和‘抑郁症’和平共处了,‘抑郁症’成了给你心灵站岗的一个守护者,它成了你的保护神。” 他欣然地笑笑:“既然你说抑郁的本质是一种对耗竭的自我调整,那我只能带着它一块儿度余生,也算我们彼此都有个伴儿。”送他出门,我看到了一个宽阔坚实的背影。装订好他的案例记录,摩挲着不同纸张上深浅不一的字迹,有点恍惚,不知不觉我们就走了八年之久。原来伴随一个人的人格成长,真的无法速成,所幸,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没有放弃。 在 总结时,他说:“我有好多次都感觉到心理咨询没有什么作用,不想过来了,可我又对自己说,再试着去一次吧,反正已经约好时间了。”我也坦诚告诉他:“好多次,我都想,把这个个案转给其他同仁吧,可我又告诉自己说,容我再找督导老师讨论一下,讨论之后,就又想着再往前走走吧。” 八年时光,我们在方寸咨询室里,“不离不弃”,共同维系着长长的一段超越所有亲密关系的特殊“亲密关系”,一同经历着生命的一次次洗礼。在咨询中,在他对自己诺大的一个人在人际互动中总是莫名其妙产生巨大的恐惧充满不解时。 我曾经临场发挥,给过他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一个人的人格成长,象身体成长一样,也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如果用俄罗斯套娃来比喻的话,那么人格比较强大的人就是一个套一个,由内到外严密地排列着。而人格比较脆弱的人,可能只有最里面的一层最小的和最外面一层 的,中间是空的,通常外面的这个大的,还不是真正的大,而是有些虚的。” 他当时眼眶发红,哽咽着说:“我就是那个只有两层的套娃,外面这一层是讨好大人们装出来的,象是一个纸老虎一样,所以一戳就破了。”我听得也很心痛,告诉他:“我们慢慢把中间空的地方都给补起来,让里面一层一层的套娃都重新长出来。”八年时光,我们彼此都见证了对方的成长。 初见他时,还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翩翩青年,不论是衣服品味还是举手投足间的气质,都在传递着他良好的自我修养,我大脑中瞬间盘旋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古诗词。同时,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在天花板上温和低沉地对我耳语:“小心,移情与反移情在你还没开口时就已拉开帷幕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 眼就让我“喜欢又欣赏”的年轻人,一直被极度的自卑感和不招自来挥之又不去的“抑郁”困扰到几近窒息。而今,送他出门时,他即将年届不惑,周身上下自有一种千帆过后的沉稳练达,他的步履是稳健又自信的。而他也陪伴一个青涩的咨询师由一腔热血一点点走到越来越谨小甚微。 祸兮福兮,隐约觉得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让二十上下这一代的年轻人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成长,至少我在自己儿子身上体会到了一些非常务实的气息。前日周末晚上,饭后的客厅,电视里正在播报着西安的疫情动态,小儿子突然来了一句:“前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差点就从武汉回不来了。” 也可能正因为他的四年大学生涯有两年是在疫情之中度过的,尤其他的大学校园又恰好位居疫情始发的武汉市,他亲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人世无常。所以,在即将告别学生生涯时,他的求职入职都表现得很有自知之明,不敢有太多的好高骛远。可能是有了比较恰当的自我定位吧,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就自己跻身入了教师队伍,我以为他只是先过去谈谈看,没想到回来就直接将入职合同摆在了我面前。 当他颇有几份自豪感地度过人生 个教师节后,便几经辗转,联系上了他小学的启蒙老师,只为报告老师,他和老师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数年不见的师生互相加了
|
当前位置: 咨询 >心理咨询师实录你终将成为你喜欢的样子
时间:2023/2/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暗藏假鞋被掉包风险,改鞋新潮背后有
- 下一篇文章: 培志笃行让世界因我而美丽,沧州迎宾路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