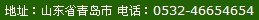|
▲艺术家徐冰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徐冰 回顾展“思想与方法”,周一至周五每天12点,都会放映徐冰 电影作品:《蜻蜓之眼》。这是一个剧情片,讲述名为“蜻蜓”的女人和爱她的男人彼此之间“寻找-迷失-寻找”的过程。 ▲徐冰《蜻蜓之眼》截图,故事从一个寺庙开始 原本在寺庙带发修行的女孩“蜻蜓”,进入社会后因普通容貌屡屡受挫,最终通过整容成为一位网红主播“潇潇”,却遭遇网络暴力导致死亡;疯狂爱着“蜻蜓”的技术男友“柯凡”为其入狱,出狱后遭遇蜻蜓的死亡,无意间看到蜻蜓整容前后的照片,决定为自己“换脸”,变成蜻蜓的样子。当他“与蜻蜓的脸合二为一”,并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他似乎懂得了蜻蜓的选择。影片结尾,他以“蜻蜓”的样子重新回到了寺院。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 柯凡即将接受整容变成蜻蜓的样子 作品的特别之处并非这个看似俗套甚至有些狗血的剧情,而是其中每帧都来自于网上公开的真实监控画面。扮演两位主角的是随时出现在监控之下的“路人甲”、“路人乙”。这是徐冰对新媒体时代下无处不在的“监控”现象的直接回应。 ▲年,位于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凤凰》 如何面对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并从其中一个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介入,最终推进到超越地方性与时代的深度,是考察徐冰创作方法论的关键指引。 ▲《天书》— 综合媒材装置、手工刻板、印刷及传统书籍装订 《蜻蜓之眼》这部新作不仅突破了徐冰以往的创作媒介,亦是其创作方法的一次“集大成”体现。在人生不同转折时期,他总是紧紧地抓住时代命脉,从小到大,从外围到中心展开工作。十年前的《凤凰》回应那个热火朝天建设的时代;占据其艺术生涯过半历程的“造字运动”,回应了现代化、互联网化之后人类文化之本——文字及语言所遭遇的困境。这几件作品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紧密相关,铺成开来,展现了一条只属于徐冰的艺术创作方法论。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 《蜻蜓之眼》:监控世界里的虚构与真实 徐冰《蜻蜓之眼》的想法源于年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监控画面。但“想拍些什么”恐怕早在20年前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当时7街的地下室很有名,不仅居住着包括他在内的一帮中国艺术家,文化名人,更是纽约和美国各地的嬉皮士、朋克等愤青 光顾的地方。地下室的入口处有一个红灯,成为流浪汉与妓女们“办事”的场所。徐冰有时出门就会碰上这样的场景,当时他就想过,要在门上安一个摄像机,也许哪天能做个什么作品。 虽然并没有真正采取实际行动,但想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二十年后,电视里的监控画面把这个想象重新调了出来。他忽然很有感觉:“如果有人用这个画面做一个剧情电影出来,一定很了不起。” “以往的电影,无论表达的是多么真实的现实,里面的人物都是演出来的,没有一帧是真实的。如果用真实的监控录像来做一部电影,作品的张力会变得非常强。”徐冰想象着。 ▲《蜻蜓之眼》截图, 每到电影中主角命运转折之时, 都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场景, 这些都是出自真实的”监控“画面 像30年前突然冒出要做一部谁都看不懂的书一样。有了这个想法,说干就干。他开始搜集一些监控资料,但过程非常困难,只能被迫停止。年年初,他和团队忽然发现网上已经有大量监控的平台出现,一搜索,发现内容比他们想象的要丰富很多,且记录的大多是超过他们认知范畴的画面。他决定重启这个项目:“当时征询了很多电影界人的意见,几乎都说不可能,因为它打破了剧情电影的很多铁律,比如要有摄影师、演员,否则电影无法推动。”徐冰谈到。 于是,徐冰有了写一个关于“整容”剧本的想法,这样里面的人物面容可以改变,有可能帮助推进故事发展。电影的制作就这样开始了。 这部电影的工作方法和所有剧情电影都不一样:“它是先有画面,然后开始剧本设计,有了简单的剧本之后,再去搜索素材,从上万个监控录像中选取画面。”在徐冰的工作室里,专门有一个房间,放置20台电脑,来完成搜索、筛选、剪辑画面的工作。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 柯凡在为替蜻蜓报仇 有时候,有些画面实在搜索不到,他们不得不改动剧本。比如里面有一段与监狱有关的剧情,原本他们以为监狱里有很多监控,结果却找不到一帧监狱的监控画面。 只能用文字“三年后”来表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在看完这部电影后评论到:“在这部电影中,徐冰首先给观众一个心理预期,文字介绍是电影由真实的监控画面组成,以为它会是一个揭露现实的纪录片,但结果却是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监控又是完全不被感知的影像,其特征应该是碎片化、瞬间的、震惊的,我们看似处在一个海量影像和真相的时代,但数码化的影像都是可以合成与改写的。徐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点,用碎片化的、真实的东西重新组合成一个有人文主题的故事。这是一件南辕北辙的事情,对观众而言,产生了一种撕扯的感觉。” 在电影背后,徐冰试图拓展的是更加意味深长有关“监控”的思考。“监控”最早是“冷战”下的概念,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但今天绝大部分的监控技术已经转化到了大公司和普通人手里,这正是徐冰《蜻蜓之眼》这部电影中所有画面素材的来源。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 整容的“网红脸”时代使”监控“失效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监控以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录像是否应该算监控?比如网红直播,它和真人秀不一样,想真实地表演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又是假的,可与她的生活又是相关的。”徐冰进一步指出。 如今,“老大哥的事”已经成为游戏和真人秀的内容,很难想象,曾经投入大量花费的“监控”活动,在“人人争当网红”,开启24小时直播生活的时代变得如此轻而易举。“面对镜头,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自己的手机唱’双簧’,向全世界发布我的动向。” “这是一个比《楚门秀》的想象更大的世界!全球成为一个大的摄影棚,我们随时都在闯入画面,演着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层面上,影片所探讨的问题成了一个全球的议题。戴锦华谈到:“如今,掌控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再是*府、文化抑或宗教,而是由无数的’监控’所产生的大数据,背后掌控的可能是资本,资本可能在无定向的流动,未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也许是《蜻蜓之眼》为我们提出的思考。 ▲徐冰与团队找到的监控画面的提供者之一 电影制作完成,为了解决之后的肖像权问题,徐冰找到了90%影片中的人并得到他们的授权同意。之所以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人,利用的也是数字技术的卫星定位。他们找到的 个人——小王,是学电脑的,大学毕业后回农村老家开了一个电脑店,但兴趣都在安装摄像头上,通过这个摄像头他的生活和世界发生了关系。徐冰和团队找到他时,他说:“也许我哪天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变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安这个东西,你们是不会从北京过来找我的。” ▲《蜻蜓之眼》相关材料: 剧本及授权同意书 徐冰咨询过的所有律师,都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他这个肖像权的边界在哪儿。“事实上,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都被采集了,大数据化了。这些大数据公司、体系从来不会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的行为构成了他们数据的价值,增加了他们的财产,却从来不会有人付给你一分钱。某种意义上,不是我使用了这些肖像,而是机器将人的肖像权利使用了。”在完成这部电影之后,徐冰说,他的团队都尽量少出门。正是深感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徐冰《蜻蜓之眼》截图, 其中一个男主角柯凡的“扮演者” 基于电影“真”、“假”的互换,使最初被所有电影导演推翻的不可能实现的电影成立。电影的开头与结尾都在寺院,结尾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既是对整个影片的呼应,也指向一个更 问题:在这个世界,真与假的边界在哪儿?这一句“了悟”的话,本身又是不可说的。徐冰看似很认真地扮演一位导演的角色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却声东击西地“表达了一种不可表达之物”。正如他最早做《天书》:用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在徐冰四十多年创作历程中,这一内在脉络一以贯之——把一个不可说的事情用艺术的方式说清楚。 这部电影的创作,从一个个碎片式的,带有具体指向的监控画面,到一部叙事完整的电影,彼此之间的矛盾,背后指向的关于整个时代,和人的更深层的思考。体现出了徐冰独特的创作方法。用他的话说是:“艺术家要把局限性的东西转化并且用好,使他变成只有你才有的东西。” “用以前的人没说过的话回应现实问题”是徐冰一直以来对自己创作的要求,在大型装置作品《凤凰》、“文字”类作品中亦是如此。 ”徐冰《凤凰》纪录片: 面对“奥运年”热火朝天的建设, 徐冰以《凤凰》这件作品对这一现实进行了回应 《凤凰》:现实世界里的崇高与卑微 与《蜻蜓之眼》一样,十年前开始的《凤凰》也是从一个局部开始铺展开来的。二者在材料与作品之间的矛盾张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冰《凤凰》纪录片,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 年,是徐冰在美国生活了18年之后再次回到国内定居的一年。曾经熟悉的城市变得陌生,“奥运年”热火朝天的建设是刚回国的徐冰对这个城市、国家最直接的感受。 ▲徐冰《凤凰》纪录片,在工地上工作的工人 作品的起始是受北京世界金融中心的委托而作,在当时北京的CBD,这些现代化、舒适,金碧辉煌的庞然大物正不断兴起。在此之外,杂乱的施工现场使徐冰更加震撼,每天在其中工作的劳动者们引起了徐冰的兴趣。年轻时作为知青的徐冰对这种景象并不陌生,对劳动人民有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他觉得可以基于这个现实进行一件艺术创作。 ▲徐冰对凤凰的研究 用什么意象来回应这一火热的“建设运动”,表达他对于劳动者的尊重?他想到了凤凰,这是中国神话中的灵兽与百鸟 。自古以来,作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符号象征,凤凰的涅槃重生,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在对各个朝代的凤凰形象进行深入研究后,徐冰选择了两只汉朝时代的《凤凰》,这一时代的凤凰最能展现被称为“神鸟”的挺胸展翅,气宇轩扬的神态。 ▲徐冰《凤凰》草图 在创作手法上,徐冰曾表示:“我希望这件作品的手段和中国最民间的方式相像,有很强的人民性。”于是,他采用了中国民间艺术选择的最朴实的材料来表达崇高的美好理想。其中又容纳了西方取现成物的方式,构成了国际性的艺术语系。更重要的是,手套、头盔、铁链、工作服、搅拌桶、铁钳······等劳动工具的材料选择,本身和当下中国所蕴含的种种矛盾、反讽,与社会现象的互相对称,使每一位在现场正视《凤凰》的观众,都能从它身上看到深厚的能量。 ▲《凤凰》工作现场 与《蜻蜓之眼》创作过程类似,《凤凰》也是在边制作边调整思路。为了收集材料,徐冰与委托方:罗芙奥集团工作团队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建筑工地,与寻找《蜻蜓之眼》的素材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徐冰请所有施工现场的工人们亲自参与作品的制作,一边实验,一边构思,一边调整, 制定出了最严谨的设计方案。这样反复的创作过程,亦如凤凰的重生。 ▲《凤凰》制作过程图- 作品的制作方法体现出徐冰在创作时的另一特质:追求 的完美。每一个材料元素之间如何衔接,呈现出怎样的逻辑关系,都是他要考量的重点,这需要众多技术的支持。既能使整个作品彼此之间不会相互抵触,各部分的衔接又能经由碰撞产生出新的含义,在美感上协调一致。这正是徐冰的独特之处:把本身不足为奇的物件,放在恰当的位置,使其成为一个极具语言能力,不同凡响的事物。 ▲《凤凰》创作过程图,- 比如《凤凰》脖子部分取自挖土机的长臂;颈部使用玻璃;羽毛则用铁锹拼接而成,凤爪是由挖土机构成,尾部由建筑钢条与轮胎框组装······ 整件作品历时三年时间, 地呈现了变化中的中国所涌动的能量。徐冰创作惯用的思想与方法亦在这件作品中展现:用最普通的材料,呈现的是与之相对的“凤凰”这个庞然之物的巨大体量。 ▲夜晚的《凤凰》通体发亮 在作品制作的后期,徐冰有了新的构思,他为“凤凰”的表面镶嵌上数以万计的LED灯。白天,这是一件带有劳动工具特有的粗糙痕迹,写实又充满野性美的凤凰;到了夜晚,它通体通亮,富有一种浪漫的面向,仿佛仙境神鸟,又如一切财富一样,富丽堂皇的外表下包裹的是残酷的现实。这一只凤凰的形象也完成了艺术家对于它最初的设想:“我希望它是浪漫、美丽,同时又是凶猛、神秘的。既怪异又现实,它用一种非常低廉的材料来打扮自己,让自己变得很有尊严,但又带着伤痕累累的感觉,这就是《凤凰》的感人之处。” ▲在夜晚,《凤凰》富有一种浪漫的面向 《凤凰》于年完成,先后在今日美术馆、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出,之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中心亮相,随后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展出,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呈现。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展出,都生发出不同的现实意义。 ▲年《凤凰》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场景 ▲年《凤凰》在MassMoCA展出现场 ▲年《凤凰》在圣约翰大教堂展出现场 戴锦华还记得自己 次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见到《凤凰》时,欧洲教堂的建筑风格与巨大的凤凰,迎着大门,在光线照射下,深深地震撼到她。站在那里的那一刻,情感非常复杂,在一千万种情感里,有一种是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而她又深知作品的材料来自中国的建筑垃圾,作品的制作是由无数双工人的手完成的。中国的农民工与龙飞凤舞的凤凰;“卑微”与“崇高”之间完成了融合与转化。 ▲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里的《凤凰》 徐冰曾说自己的本事就是牢牢抓住时代,作为回国后的首次创作,《凤凰》很好地回应了中国作为全球最有实验色彩的特点,抓住了中国迅速变化的脉搏,使徐冰成为一位 实验精神的艺术家。在“文字”类的作品中,面对不同的生存处境,艺术家则用创作回应了他所面对的现代性、当代性、国际化的问题。 ▲徐冰《天书》— 综合媒材装置、手工刻板、印刷及传统书籍装订 “造字”:《天书》、《英文方块字书法》、《地书》全球语境下的传统与当代 将所有命题回到媒介,从材料本身出发,去做与其表象完全相反的事情,是徐冰的艺术创作一贯在做的事情。无论是其前两件作品,还是关于“文字”的创作,恰当地表明了这一特点。 徐冰将这一方式总结为“声东击西”,看似在认真做这件事情,其实在说另外一个问题。就像许多人最初看到徐冰的《天书》,以为这是关于中国传统的讨论,但实际上,“他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对五四以来传统的粉碎。”蔡锦华谈到。 《天书》是徐冰研究生毕业后创作的 件作品,这件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为:“用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他造了四千多个假字,装帧成古籍的样式印刷出来,别人都以为这本书一定很重要,里面会有精彩的内容。实际上在吸引人阅读的同时,又拒绝人进入。徐冰讲述的是比书本身更有内容的内容。 ▲《天书》细节 为什么要造这样一本书?与徐冰一直以来跟文化之间的“别扭”关系有关。徐冰生于一个学术严谨的家庭,成长于一个特殊的追求*治正确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字一直具有很高的地位。徐冰同样对文字有一种崇敬之情。然而,在他开始学写字时,正值简化字运动,一批批新字公布,旧字废除,对新字的再更改和废除,对旧字的再恢复使用,把他们都搞糊涂了。在他最初的文字概念中,埋下了一种特殊的基因:颠覆——文字是可以“玩”的。 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对文字的力量“心有余悸”。因为父母都在北大工作的关系,徐冰很早就接触各种书,“那时候小孩子读不懂,等到能读懂的时候,又没什么书可读”。但“文字作为人类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却深印在徐冰心里——触碰文字就是触碰文化之根本,对文字的改造是对人思维最本质的那一部分的改造,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深谙此道。这种改造是触及灵*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天书》不能读,却有着书严密的逻辑结构: 从书名到页码、目录、注释等, 是一本谁也读不懂的“真正的书” 徐冰懂得触碰文字的作用,既充满敬畏,也不无调侃。制作《天书》便是源于一个奇思妙想:做一本谁也读不懂的书。这本不能称之为“书”的书,有着书的严密逻辑与结构:书名、册序、页码、题目、总目、分目、总序、分序、跋文、注释、眉批、段落终止等。徐冰花了两年的时间刻完了多个假的字,这是日常读物上出现的字的数量;字的笔画按照《康熙字典》从少到多的序列关系而造;字体选择的是所有正式文件中使用的,不具任何指向的宋体。 而整本书的制作过程决定了作品的命运。徐冰认为:假戏真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艺术的力量就会出现。“认真的态度”在这件作品中,是属于艺术语汇和材料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造字的过程,还是之后的印刷过程,徐冰的“完美主义”要求都发挥到了 。 ▲徐冰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的《天书》活字原版 徐冰采用的是活字印刷的方式,其中涉及的排、校、改、拆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当时徐冰全身心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全不为身边的知识分子奔向现代化狂热的阅读、研讨的热潮所动。他在自己十平米的工作室里,享受着一种封闭的崇高感。 印制是另外一件麻烦的事情。那时为了找到一个符合古籍印刷的地方,他要跑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这儿要先坐长途汽车到一个地方,然后租自行车,骑两个小时才能到。在后来印制的两年时间里,徐冰平均每个星期就会跑一趟,为了保证完美的效果,有时一点细节处的变动他都会亲自跑一趟。在往返之间,路两旁的树从嫩绿、深绿、*、深*,再到黑、白, 回到嫩绿······后来《天书》随徐冰出国并在全世界各地展出,广受好评。这件作品不仅决定了徐冰今后创作的基本方式与思路,也奠定了他后续“文字”作品的创作基础。 ▲徐冰:《英文方块字书法》 《英文方块字书法》的创作是在徐冰去美国之后三年开始的,那时他正遭遇语言困境,与徐冰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关系:“你的思维是成熟的,但说话与表达的能力却是幼儿的。你是受尊敬的艺术家,但在那个语言语境里,又是一个’文盲’。” 去了美国之后,徐冰所生活的环境与状态实际上是两个文化的中间地带:身边都是熟悉的艺术家,但都处于异国他乡。“生活在哪儿,就面对哪儿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虽然生活在纽约这个国际化的都市,但因为彼此不同的背景,徐冰所面对的问题与其他的艺术家是不同的。 ▲《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 徐冰用中文方块字书写的英文字母 基于以前《天书》时期对文字的研究,徐冰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用英文做一些东西。通过许多尝试,使他逐渐了解到不同语言特征,并想到了两种文字“嫁接”的可能性。英文是线性书写的拼音文字,中文是方块形式的文字。有趣的是:这样的转化使熟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在其面前都变成了“文盲”。与《天书》不同的是,《英文方块字书法》是可阅读的文字,而为了“扫盲”,徐冰专门写了一本讲述如何写这种书法的教科书,题为《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并且在每次展览时设置一个观众可参与的教室形式。作品没有西方当代艺术系统“深奥”的理念,却拓展了人们的思维:书写这类文字时,脑子里想的是英文字母,同时又要顾及中国书法运笔的讲究。 ▲“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现场之 《英文方块字书法》教室- 这个教室先后在全球五十多个地方展出,所到之处都有很好的反响。尤其对年轻的学生而言。一次徐冰在日本福冈的一所中学教授了这种书法之后,一个学生说:“从今天起,我学到了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我过去所学的知识。” ▲在学习《英文方块字书法》的观众 这件作品,徐冰希望探讨的不仅仅是中西方语境下文化的交流、沟通、碰撞、融合,而是通过作品向人们提示一种新的思考角度,改变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当代艺术的新鲜血液经常是来自艺术之外,又回馈于社会。《英文方块字书法》的实用性与在艺术体系之外的可繁殖性,是徐冰尝试的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徐冰作品《地书》,年上海版本(退底)。 他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标识和各种领域的符号, 做了这本说什么语言的人都能读懂的书 徐冰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造字运动”在其《地书》中真正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最理想状态。工作的关系,徐冰常年在全世界各地飞行。年的一天,当他在飞机上留意到一些用符号标识的指示系统说明书,简单的几个图形就达成了全世界说着不同语言人之间的“共识”,这一点瞬间吸引了徐冰。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发现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标示图形:口香糖包装纸上的几个小图,就可以知道(要把用过的胶状物用纸包起来扔在垃圾桶里)。“既然只用几个标识就可以说一个简单的事情,那么用众多的标示一定可以讲一个长篇的故事出来。” ▲徐冰《地书》收集的标识系统 从那时起,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标示,也开始研究各个专门领域的符号。 在数字互联网技术迅速拓展的今天,几个简单的表情就能成为人们交流的工具。随着新的数字产品中标识大量的出现,使得这项收集变成无止境的工作,也让徐冰更加意识到它的意义所在。在《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是人类语言被打乱的开始,而多少年来“普天同文”的理想,在如今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读图时代被真正激活。正如人类最初用图来表达各种含义一样,在经历了开化到文明的几千年时间之后,徐冰认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某些层面上带有可考的最早时代的特征:每天都有新的技术与新工具发生,这些东西具有突变性,是突如其来的。世界变得陌生如初始,挑战着每一个人对新的、不熟悉的生活环境的接受度。今天成了新一轮的象形文字的时期。” 基于收集到的一系列标识性的“文字”系统,徐冰创作了《地书》。与《天书》不同,它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阅读的书。最早的一本《地书:从点到点》讲述了一个上班族“小黑”的一天,这个故事被翻译成中文有一万四千多字。这些简单的标识符号竟然有如此强大的表述能力,是徐冰之前没有想到的。 ▲徐冰《地书:从点到点》, 中文翻译:走出厕所, 小黑一眼看见猫大人的眼睛在角落里盯着他, 他突然想起来还没喂猫呢! 赶紧把猫粮倒在盆里,猫大人慢悠悠地吃去了…… 从《天书》到《地书》,这些异样的“文字”有着共同之处:它们挑战知识等级,试图抹平地域文化的差异。《天书》与《地书》比起来,更像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从里到外都是用传统的手段制作的。它所引发的讨论无论怎样展开,其物化的作品方式都是传统的。而《地书》作为一个艺术项目,由于它的“实时性”,使它成为一个不会结束的项目。而且它本身是“发散的”、“不固定”、“无形态”的。 这正是徐冰艺术的追求:艺术重要的不是像与不像艺术,而是为这个系统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带给更多的人启发。这一点,无论是从《蜻蜓之眼》往回追溯,还是从《天书》往后推导,都是如此。 ▲“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现场 UCCA徐冰 回顾展命名为“思想与方法”,是徐冰艺术恰如其分的总结:对他而言,艺术不是思想到思想再回馈思想,而是从手艺到思想,再指导手艺的记录。对时弊的感知、思维的推进,有时是无意间看到的某个画面/事物展开的;有时通过对某栋新楼的造型、材料、颜色或与周边建筑关系的判断展开的,有时是通过在工作室反复摆弄手里的“活儿”展开的······ 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每一位艺术家都面临来自自身、环境、时代的现实问题。徐冰对社会问题的回应,首先在于他敏锐的感知,与 的把握,从一个局部出发,对材料深入研究,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收集、整理的工作,基于这样的积累,建构出一个更完整、丰富的作品体系。而他惯用的”声东击西“的方式,将所有命题回到媒介再返回媒介去做与表象相反的事,对”艺“、”术“之间调配与平衡的追求将思想延展开,从局部进入将作品推进到跨时代的深度。借由三件/类作品,以时间倒叙进行追溯,使我们看到了这位超越于时代艺术家独特的方法论。 参考资料:徐冰《我的真文字》 徐冰《凤凰》相关画册 徐冰《台北市立美术馆回顾展》画册等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13801256026.com/pgsp/2679.html |
当前位置: 咨询 >徐冰创作方法论声东击西地介入社会和超
时间:2023/2/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商业秘密鉴定提醒以下行为可导致商业秘密
- 下一篇文章: 职场上,阻碍你前途进步的往往不是大事,而